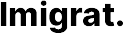八十年代中期,四川乐山大佛率先开始收起了门票,在此前,宗教场所都是没有门票的。第一个吃螃蟹的乐山尝到了甜头,在九十年代初期,每年都能供应两亿的收入。别的地方看到乐山这么赚钱,也纷纷在寺庙搞起了收门票的生意。这就是佛教商业化的1.0版本。寺庙赚得盆满钵满引来了民间资本的垂涎,大量的民间资本开始进入寺庙投资,进入各种重要建筑。比如2002年开工建造的河南平顶山大佛景区,耗资约二点八亿元,前后历时五年。
大佛建成后,想要参观,除了每人收一百二十元门票,还有其他各种敛财办法。比如到佛像下摸一下脚,号称可以获得佛祖保佑,但要额外收五十五十块钱就能收买佛祖,也太瞧不起我佛了吧。平顶山大佛的建成开启了佛教商业化的2.0时代,不过这远远不是终结。很快,佛教商业化迎来了三点零时代。收割信徒毕竟摸一下佛祖的脚就要收五十,一般人充其量呢也就被收割一次,绝不会有第二次了。
想提高反复收割的几率,最好把目标瞄准信徒这一波收割主要就是出租灵位,也就是南京玄奘寺这种方式相比收门票钱这种方式的吃相相对好看,但利润更高,高达百分之五十以上。除此之外,还玩起了拍卖投注箱。二零零八年,寺庙第一次组织投注箱拍卖就卖出了十万,随后投注箱的拍卖价一路狂飙。二零一一年甚至卖出了一百一十八万的天价。商业化3.0时代的佛教,其实已经不再是宗教场所了,很多寺庙的背后都是企业投资的。
你以为寺庙的负责人是住持,实际上很多寺庙住持都是打工人给企业打工的,每个月都有k p i 考核制度,但是一切都怪资本吗?显然不是佛教自身的集体性迷茫才是关键。为什么说佛教已经陷入了集体性迷茫呢?一切还得从佛教的历史说起。佛教自从传入中国后,其本质上是与其说是一种宗教,不如说是一种基层组织形式,类似于村庄的基层单位。水浒传里,鲁智深失手打死了政徒,不敢留在城里,就通过员外的关系出家到五台山文殊院。
在那个皇权不下乡的年代,文殊院这类寺庙和香山一样是地头蛇。住持实际上起到了村长的作用,方圆十里八村都是他们的十里范围,官府一般不会惹他们。所以鲁智深只要进了文殊院也就安全了。
而在新中国建立后,党支部深入到了基层,乡村被消灭,寺庙也一样,没法再像过去那样当地头蛇了。也就是说,在基层政权体系中已经不需要佛教了。失去了在基层政权体系的位置,佛教便从政权体系中完全退出,不再是国家统治阶级的一员。更沉重的打击是改革开放在以前,穷人们之所以愿意去当和尚,看中的就是寺庙里有饭吃,饿不死,斋饭也是饭嘛。
而改革开放后,人们生活水平日渐提高了。寺庙那点儿伙食对穷人失去了吸引力。在日常生活中,人们已经不需要佛教了,可有可无,直接导致佛教的社会中失去了生态位。作为对比,新教在美国红洲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。比如很多红洲的教堂,平时依然是红脖子们的主要聚集地,新同学们来这里唱诗,参加集体活动,以此塑造集体感,给人们以心理慰藉。由于有这个生态位,所以新教在美国依然保持活力,商业化也相对没那么严重。
佛教找不到自己在社会中的生态位,唯一能找到生态位的只有旅游景区。这也是佛教商业化的根源,除了充当旅游景区,佛教已经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了。
那么,社会中有哪些生态位是适合佛教去探索的呢?像以前那样成为一种基层组织,绝无可能世俗化国家不会允许宗教在基层把持政权,真正适合的道路就是慈善。
我们一定看到过类似的新闻报道,美国的某个教堂向穷人派发救济物资。当今的基督教就是这样,既然已经不可能成为政权的一部分,那就靠慈善维系自身的存在。毕竟确实有很多人需要帮助,政府,也不可能全都帮助。
这时候佛教如果能提供一份力量,当然是好事。在这方面佛教能做的事情很多,比如佛教寺庙一般都有藏经阁,那把藏经阁改造成图书馆,供人们阅读也未尝不可行。我国2020年公共图书馆合计三千两百余个,只有美国的五分之一。如果算人均,则差距更大,别说很多农村孩子接触不到图书馆,就是不少的县城。三四线城市公共图书馆也不多,盈利性的图书馆书籍多数都是教辅书。你想坐下看书,先要点一杯40块钱的咖啡。这一切严重阻碍了知识文化的传播。
佛教如果能站出来多建几个图书馆,特别是在乡镇、县城和贫困的地区,对当地人将是一大利好。我相信政府也是欢迎的。当然藏书要多一些,社会性书籍不要那么多。宗教典籍除了图书馆,佛教能做的慈善还有很多,但这一切需要佛教重拾初心赚钱赚得太多了。不知道初心还在不在。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